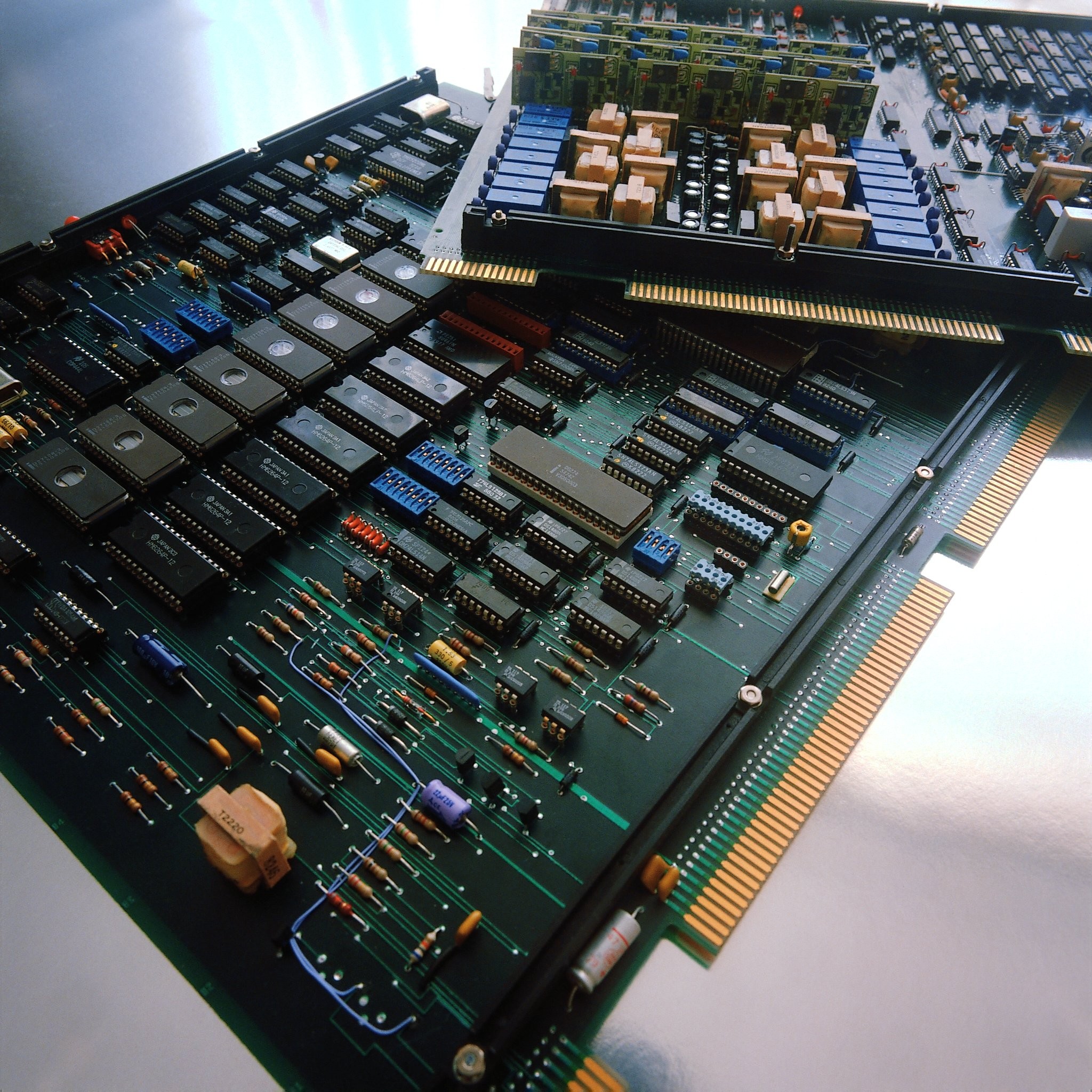关于东晋之际的门阀政治体系,被视为变态、畸形发展的政治体系,但其出现并非空穴来风。
其一,东汉末年,士人清议之风盛起,出现了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局面,士人之间互相品题、共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普通士人一旦为名士所赞赏、品题,便如登龙门,身价倍增,千里求名之举亦不鲜见。尽管汉末党锢之祸对于士人清议进行了严酷镇压,但却加强了士人群体身份的认同,构成汉晋时代“士的觉醒”的重要面向。后来随着一系列事件,此时进入三国鼎立时代。其时曹魏举荐人才的主要方式之一便是名士品评、提携同郡士人,例如当时司马懿曾被同郡河内杨俊、清河崔琰所举荐。通过互相的举荐和品评,可以加强同乡同郡之间的家族关系,并且品评人和被品评人也可以在朝廷中为自己增加政治资源。例如,《三国志.杨俊传》中写道:
黄初三年,车驾至宛,以市不丰乐,发怒收(杨)俊。尚书仆射司马宣王、常侍王象、荀纬请俊,叩头流血,帝不许。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杀,众冤痛之。
司马懿、王象、荀纬三人皆为河内人,自然不是一种巧合,体现出同乡官僚在政治上互相支持与提携。其时家族之间的互相品评、联姻,来上升或者加固大族的地位并且由此进行入仕,这无疑可以看做是魏晋时期阶级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魏晋嬗代发生在三国鼎立之际,其时魏国仍然强敌环伺,蜀将姜维频频北伐。所以魏晋嬗代之际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清洗。例如高平陵事变,虽说“同日斩戮,名士减半”,但其所株连多是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之人物。其时仍然大多曹魏元老仍然“心存曹氏”,大规模地进行政治清洗也会使曹魏功臣对司马氏心存憎恶,甚至可能进行政治变动,因此司马家族事实上并不具备大规模政治清洗的客观条件。而曹爽的改革正是由于开罪了曹魏功臣集团,才给司马懿带来了可乘之机。作为这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曹爽的前车之鉴,对于司马家族而言显得格外深刻,这也使司马氏更加深切地认识到这些功臣贵戚子弟在曹魏政治中所具有的盘根错节、不可低估的整治潜力。因此,拉拢而不是打击曹魏贵戚子弟成为了司马氏的既定策略,这些曹魏贵戚子弟只要在政治上表示支持司马氏,无论是主动还是勉强,甚至是被迫,只要对司马氏家族专权的局面表示默认,司马氏一般都予以宽容。
因此,在曹爽败亡后,司马懿只是对与其关系最密切的何宴、邓飏、丁谧、李胜等人痛下杀手,而对于曹爽阵营里的声望最高的夏侯玄仅以闲职处之。因此,司马懿上台后的政治诛杀,表面上看来株连不少,但除了曹爽一支外,并没有损害曹魏政权中原有的的权势网络。很多士人虽然曾仕于曹爽,但很多并未遭到株连和问责,很多后来都逐渐转变为司马氏之臣,甚至贾充还成为了司马氏的心腹。
其三,各个世家大族通过品评、联姻等方式进行家族之间的联合,逐渐成为了地域与文化乃至政治方面的认同。出身世家的士人看不起出身寒微之人,对他们在政治上屡加排挤。而由于宗室、功臣形成了一股政治平衡,根基未稳的司马氏亦不敢开罪世家大族。
例如,曹魏在伐蜀战役中,根据钟会的谋划,魏军最初的战略意图是发动一个钳形攻势:钟会统帅伐蜀部队的主力十余万,从骆谷、斜谷的大路进取汉中;邓艾与诸葛绪各统军三万人从陇西进攻,进行战略牵制。邓艾进取甘松、沓中阻挠姜维的行动,诸葛绪进占武街、桥头切断姜维的退路,前后夹击,阻止姜维退向汉中,以使钟会率领魏军主力能够迅速占领汉中,打开进攻成都的通道。但由于诸葛绪在行动上的犹豫,差了一日的行程而未能阻截到姜维,姜维得以成功地从桥头突破,引军退往剑阁,依仗天险,与钟会率领的魏军主力相持。按照原计划的安排,邓艾本来应该和诸葛绪一样,引军东向,与钟会率领的主力会师,因为在伐蜀战役中,虽然名义上是“诏诸君伐蜀,皆指授节度”,但实际上钟会是这场战役的真正领导者。但由于姜维已抢先一步退往剑阁,据险防守,魏军原来的战略意图已无实现的可能,邓艾向东与钟会会师,并无实际意义。
因此邓艾决定改走阴平小路,穿越七百里的无人山地,绕过姜维所驻守的剑阁,直取成都。邓艾果敢的军事行动使他统帅的这支偏师立下灭蜀的首功。但是由于邓艾此举的确违背了事先的计划,尽管他在行动前曾上言司马昭,但却并没有知会钟会,钟会作为这次伐蜀战役的策划者与领导者,最终却无功而返,这对于一向骄傲自满的钟会而言无疑是个不小的挫折,钟会是一个权力欲和报复心强的人。并且由于邓艾在灭蜀之后专擅独行,“辄依邓禹故事,承制拜刘禅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督。蜀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署。以师纂领益州刺史,陇西太守牵弘等领蜀中诸郡”,在处理善后事宜时,丝毫没有征询钟会等人的意见,使得邓艾钟会的关系迅速破裂,于是钟会、卫瓘向司马昭献言,致使邓艾及其子被杀,其子弟皆流放边境。然而钟会谋反之罪,只株连了直系子弟,颍川钟氏地位受影响则有限,而邓艾仅仅以专擅之罪,不仅祸及家族,就连后来为其平反都困难重重。
《三国志.邓艾传》中写道:
泰始元年,晋室践祚,诏曰:“昔太尉王淩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卫。征西将军邓艾,矜功失节,实应大辟。然被书之日,罢遣人众,束手受罪,比于求生遂未恶者,诚复不同。今大赦得还,若无子孙者听使立后,令祭祀不绝。
赦免在魏末反对司马氏诸人的后裔,是西晋立国之后争取人心的一项举措。准许给邓艾立后,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在诏书中依然强调“矜功失节,实应大辟”。在邓艾“悖逆”的罪名无法成立的情况下,依然认为邓艾之死是罪有应得,更为奇怪的是诏书将邓艾与王淩归为一类加以处置。王淩是试图推翻司马懿执政地位的人物,对于司马氏政权来说,其罪孽无疑要比邓艾深重得多,但根据诏书的解释,王淩当年谋废齐王芳之举,因为后来齐王芳本人被司马师所废,竟然变成了一次政治正确的举动,显然这是司马氏为了减轻王淩的罪责而特意发明的借口。司马氏为什么急于给反对过自己的王淩平反,而对为司马氏立下大功的邓艾却如此吝啬?其根本原因恐怕在于,王淩本人与司马氏家族及西晋官僚集团有着很深的渊源,其子王广亦是名士,王淩、王广虽被杀,但是他们的故旧殷勤依然是司马氏需要倚重的力量。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晋武帝不惜屈尊降节,亲自前往琅琊王妃处见诸葛诞之子诸葛靓,与之修好。嫁给琅琊王司马伷的诸葛靓之姊,为其子司马觐取字为思祖,其所思者正为其外祖诸葛诞,这几乎是公开向司马氏叫板,而武帝依然不以为忤。因为诸葛诞同样也是魏末人士的领袖,琅琊诸葛氏更是一个在汉晋之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名门望族。同样是涉及淮南叛乱,司马氏却从来没有想到为毋丘俭平反,在此厚此薄彼的背后有着非常微妙的政治考量。
而后来的石苞、王濬、张华等人皆出身寒微,其政治遭遇也与邓艾类似。
由此可见,魏晋虽然经历了由曹氏入司马氏的转变,但实际上由于司马氏并没有进行大规模政治清洗的条件,所以必须不断同世家大族进行妥协,并且,由于晋朝沿用了曹魏的制度,使得朝中政治门阀盘根错节,世家大族在文化、政治层面上均实现了认同,对于寒门士子多加排斥,抹杀了寒门士子的晋升之路,因此西晋刚刚建国,却显得垂垂老矣。虽然晋武帝司马炎在平吴后建立事功,声望大涨,并引入外戚弘农杨氏来抗衡宗室与功臣。但其坚决要将齐王司马攸外徙,使得宗室中两位最具才望的藩王司马攸、司马骏忿恨而死,重臣羊琇、向雄忧愤而卒;郑默、曹志等九人被免官。使得本来就盘根错节的政治局势更加动荡不安。由于晋武帝引入、培育外戚,使得其死后杨骏矫诏夺权,虽然其在夺权之后,对于功臣多加优渥对待,但由于世家大族均对杨氏心存不满,这些举措也并未收买到人心。朝中上下的不满情绪被皇后贾妃利用,使得贾后得以发动政变,尽诛杨氏一族。同时又由于贾后擅杀太子司马燏,使得宗室震怒,赵王司马伦由此入京,几百年动乱的大乱局由此肇始。